格列卫贵的原因!研发到底花了多少钱?
在谈格列卫之前,我想我们有必要谈谈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粒)。
在我的简要认知里,这曾是一种平均生存期只有3、4年的疾病。慢粒慢粒,起病慢,前期症状并不明显,但一旦进入急变期,患者很快就会死亡。
再谈谈格列卫
先说一个常识,新药研发从药物化学结构上的成功研发,剂型确定,上市前的动物实验,到四期临床试验确定安全性、有效性......最少也得10年时间。

而格列卫,诺华研发,通用名叫“甲磺酸伊马替尼片”。问世于上世纪90年代,2001 年上市,但它在美国的专利保护 2015 年就已到期。
成本很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前期研发过程中大规模地试错
在进行II期临床试验时,花在被试病人身上的成本
FDA严苛的审核标准,失败率高
研发成功药物的盈利需要覆盖研发失败的成本
那么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就格列卫这款药物,研发环节到底花了多少钱?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再讨论诸如专利保护期、药企定价是否太高、政府管制是否太严才更有依据。
早在2013年4月,美国一个NGO(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的调查员James Love就通过调查分析得出结论:格列卫的研发成本大概在3800万美元到9600万美元之间。
计算过程主要考虑了以下五个因素:
早期的研发成本
II期临床试验的成本
政府对于“孤儿药”(Orphan Drug)的税收优惠
研发失败的风险成本
研发资金的机会成本
采取的计算公式为:
(每个志愿者的成本X志愿者的人数——政府税收优惠)X研发资金的机会成本/研发失败的风险成本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3800万美元到9600万美元之间。
早期的研发成本
格列卫的早期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在美国俄勒冈州卫生科学大学(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完成的 ,主要负责人是德拉科教授(Brian Druker),并且成功通过FDA I期临床试验。在这一阶段的研发费用来源是:
50% 国家癌症研究中心(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30% 白血病和淋巴瘤协会(Leukemia and Lymphoma Society)
10% 诺华(Novartis)
10%俄勒冈州卫生科学大学(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
所以在早期研发成本主要是由科研机构和大学承担的,诺华公司并没有出多少钱。所以主要计算的是II期临床试验的研发成本。
II期临床试验的成本
经过I期临床试验之后德拉科教授认为格列卫(当时还是代号 STI 571)非常有前景,他极力说服诺华公司继续研发下去,做II期临床试验。最后,诺华一共做了三次II期临床试验,一共有1028位被试志愿者。
这个阶段的支出主要是诺华公司承担的,也是这个研发环节的最大头。所以我们必须估算每一位被试志愿者的成本,从而得出一共1028位志愿者一共花了多少钱。
根据当时的期刊和调查,每个被试志愿者的研发成本有三个信度比较高的数据:
$23527。 DiMasi在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2(2003) 这本期刊上发表的数据,从I期到III期临床试验,每个被试志愿者的成本在23527美元。
$10000。 Robert Kramer 在Parexel Pharmaceutical R&D Statistical Sourcebook 2002 这本期刊上发表的数据是每个被试志愿者的成本在10000美元。
$3861-4919。 NIH DCP Cooperative Group 公布的数据是每个被试志愿者的成本从1993年的3861美元到1997年的4919美元。
暂且不看最低的NIH给的数据,得出一个区间值:约1000万美元到2400万美元。
政府对于“孤儿药”(Orphan Drug)的税收优惠
所谓孤儿药并不是孤儿服用的药,而是针对一些威胁生命的罕见病研发的药物。罕见病的患病人数少,买药的人少,药企研发动力并不强,但是如果罕见病没有相应的药物的话,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所以政府针对这类“孤儿药”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不过诺华公司声称自己在格列卫的研发环节并没有享受税收优惠,姑且就算这一项的数据为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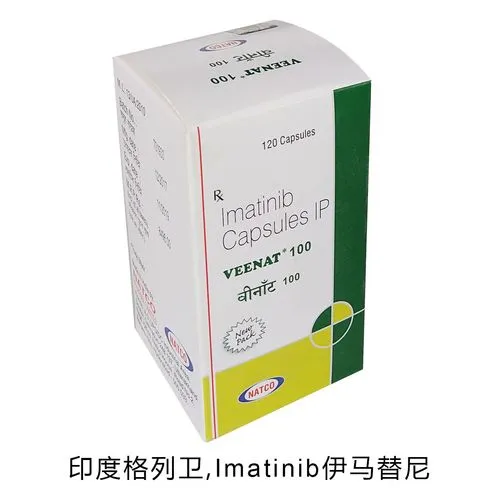
研发失败的风险成本
诺华并没有披露它在研发失败的药物上一共花了多少钱,我们就参考同时期的整体数据,相信诺华作为国际制药巨头,应该和平均值没有太大出入。
从1990年到2000年,687个孤儿药物研发最终被批准上市的只有159个,成功率只有23%。值得注意的是23%的概率是指从I期临床试验到上市的概率,而诺华只负责了II期临床试验到上市这个研发环节(格列卫没有进行III期临床试验就被批准),所以我们应该计算的是通过临床I期试验之后,成功批准上市的概率。
虽然这个概率并没有现场的数据,前文提到的DiMasi在2003年的一篇论文中写到从I期临床试验到II期临床试验成功的概率是71%,全流程的成功概率是21.5%。(与23%略有出入,按照同一数据来源的数据来计算概率)
现在知道了I期试验到批准上市的概率是21.5%,I期到II期临床试验的成功概率是71%。所以诺华负责的从II期临床试验到批准上市这个阶段的概率是21.5%/71%=30%。
研发资金的机会成本
所谓机会成本也就是这笔钱诺华如果不用来研发格列卫,用来投资或者做其他增值的事情可以获取的收益。一般药物的研发周期是90.3个月,资金成本大概是11%,而格列卫的研发周期只有35个月,我们姑且按照11%到20%的资金成本来估算。
现在我们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完毕,根据文章开头的公式:
(每个志愿者的成本X志愿者的人数——政府税收优惠)X研发资金的机会成本/研发失败的风险成本
最大值:(23572X1028-0)X(1+20%)/30%=96928064
最小值:(10000X1028-0)X(1+10%)/30%=37693333
所以得出了文章开头的结论:格列卫的研发成本大概在3800万美元到9600万美元之间。当然,这个估算肯定更不是非常准确,但至少在数量级上是没有问题的。
而我们反观格列卫的销售额,2012年一共是46.75亿美元,诺华每13天就能从格列卫这款药获得1亿美元的收入。
伊马替尼就是格列卫
随着近几年仿制药的上市,格列卫的销量也开始下滑,不过格列卫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500亿美元,已经比研发出城高出几个数量级了。
在一个非自由市场的环境中(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药品都是一个政府强监管的市场,有各种各样的审查和门槛),诺华如此定价,是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呢?
川普对于辉瑞的药价也有意见
先说国际市场上仿制药

这里有一个专利期的问题,过了专利期,原则上就可以生产了。比如“印度仿制的“格列卫”,瑞士诺华在中国的专利期已经在2013年过期了,这时候我们如果生产,就是仿制药。
而印度在其专利期内就可以生产而不被国际社会制裁?为什么我们不生产?
先说专利强制许可
其一,“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简单地说是不经过专利人许可,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某项专利。这也是世界通用的对专利权限制的规则。 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平衡公共健康和专利保护的关系上,和发达国家经过系列艰苦谈判,达成的一种“严格限制下的平衡”,当然里面也有诸多制约因素。泰国和巴西等政府对高价专利药,频频颁布强制许可。
正是因为强制许可对于国际制药巨头的威慑力,不少国家政府也经常利用强制许可作为筹码,迫使外国制药厂降低药物价格,使本国民众受益。例如泰国卫生部长称,两年前,美国制药公司从不愿接受泰国的邀请就药价进行协商,但现在就容易多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启动过强制许可,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南非、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等。
而我国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但至今为止,中国从来没有启动过强制许可机制。至于原因,按业内人士说法“这太复杂了,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利益。”
现实是,格列卫世界上中国价格最高。
延长专利保护期
其二,略微调整药物的方式来申请延长新的专利保护期限,以获取高额回报,这是跨国药企的常用手段,格列卫最早的保护期已到,而印度不承认这种微调。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诺华抗癌药格列卫在印度延长专利申请败诉》。
所以印度连强制许可都不用实施,当然,印度也经常使用强制许可制度,这让印度成为了世界药房,走向世界,也走进了美国。值得说明的是,印度这样做是符合WTO原则的,让穷人吃的起药,这也是合情合理且合法的做法。
再说我国为什么我们不生产?
从理论上说,哪怕瑞士诺华公司的相关抗癌药物仍在法定专利保护期限内,我国政府也可以出于保护“公共健康的目的”,授权给我国一些药企使用印度诺华的专利技术,生产相关仿制药。而现在情况是,瑞士诺华在中国的专利期已经在2013年过期了,而我们依然没能生产出来。
其一,我们基本没有这个能力
前文说到我们几乎所有的药都是仿制药,其实只是一种模糊的说辞。我们生产的药,还达不到仿制药的标准,仿制药有仿制药的标准,而我们国家有我们的标准。我们现在吃的药,和国际上说的仿制药是两个概念。
仿制药依然需要大量的科研,需要技术,需要人才,需要时间,当然,更需要钱,花费依然不少。我们的药企,说大而不强都是一种错误,应该说是不大,也不强。我们的药企的微利让他们很少有这个资本去研发。我们的药企在强势的医院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夹缝中是个弱者,怎么能生存能生存下去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因素。所以他们拼的是市场竞争,拼成本控制,拼销售网络。而研发,基本上是一种奢望。
中国仿制药质量标准只“看脸”,为了合格而检测
仿制药是指专利药品在专利保护期结束后,不拥有该专利的药企仿制的替代药品。由于中国药企无力自主研发化学药品,仿制药成为中国药企的救命稻草。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规定,只有在活性成分、给药途径、剂型剂量、使用条件和生物等效性上都和原研药一致,才是合格的仿制药。
而中国现行的仿制药质量标准主要看活性成分和外观、性状是否和原研药相符,而对仿制药和原研药在给药途径、剂量、使用条件和临床效果上的一致性标准“仍在探索”。
其二,我们繁琐的审批制度
我们药监局负责审批的人员包括行政也只有120人,参加一线工作的更少。导致审批太慢,药物批文的排队积压比北京深圳的汽车塞车严重的多。
一药企董事长表示:“我们的仿制药同时向欧洲、美国申报,欧美肯定比我们还快,我们中国5年以后甚至10年以后才能拿到批件。”
一家药品研发机构的负责人:“以目前的审评速度,光拿批准文号就得等16年”,其对记者这样说。
当然,以前我们的药物审批也快过,一年批准一万多种新药的情况也有,当年是什么速度?当时本人同事开玩笑说过这样一句话,这要审批人员一秒钟看一页纸,天天24小时还不能停。本人查过,同年的美国新批新药的数量都不比我们的一个零头。现在看来,又矫枉过正了。好在是,现在审批人员的配置还是大大增加了的。
其三,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仿制药生产体系
这个里面太复杂,我只能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为什么东莞那么多鞋厂电子厂不能到内地人工更便宜的地方生产?原因之一是产业链。
一个医药的加工制造,需要很多东西,有软件的,有硬件的,有医药原料,也有医药辅料中间体。我们没有自己的体系,虽然我们也比着葫芦画瓢地学习并实施了GMP,GSP,但是真正的GMP离我们有多远?业内人员必然清楚,我也不想一一歪楼了。
国产药就是仿制药吗?我们97%的化学药确实是仿制的,但我们和国际上流通的仿制药是两个概念,应该叫模仿药更为妥帖,这里面标准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药品的生产向仿制药靠拢,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上一篇:瑞戈非尼与安罗替尼的区别和认识
下一篇:肝癌耐药后的新选择 瑞戈非尼
免责声明
由本文所表达的任何关于疾病的建议都不应该被视为医生的建议或替代品,请咨询您的治疗医生了解更多细节。本站信息仅供参考,医康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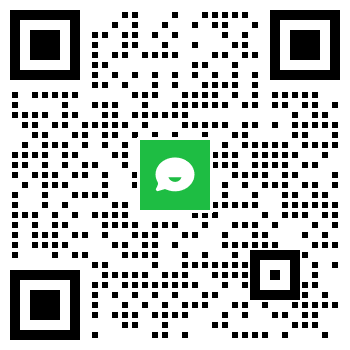
扫码实时看更多精彩文章
